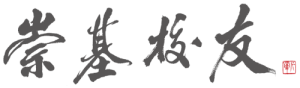出走,是為了…… — 梁嘉麗(2004/社會學)
旅行的意義 統籌及整理︰梁嘉麗(2004/社會學)、麥嘉輝(2016/新傳) 凌晨四時,我在蒼涼的西藏街頭,跳上預約好的電召車。殘舊的車子向着山中密林駛去,穿過一些村落,前路一片漆黑,只有車頭大燈照着前路。這時司機突然煞停車子,原來小路上橫躺着一棵大樹,是昨夜的風雨把路旁一棵大樹吹倒了。前無去路,我們唯有繞另一條路走。時間一分一秒過去,我心急如焚,十分擔心能否趕及。車子疾走在蜿蜒的山路上,下車時,天邊已呈現一片魚肚白。下了車,我踏着泥濘,慢慢往上攀登,往廟宇的後山走去。頭上數十隻禿鷲在盤旋着,而且不斷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聲,我腳下卻每一步都踏着不知名的白色碎片。身邊有藏人經過,步伐沉重,揹着大包,一直走上山。當我到達山頂時,天已亮了,眼前出現一片平地,中間空曠的地方呈圓形,正中央則放着幾塊大石。剛才那個從我身旁走過的藏人,這時把大布包放在空地上,附近還有幾個人放下同樣的布包,然後離開。禿鷲漸漸聚集在平地的另一邊,睜着圓圓的大眼,蓄勢待發。 天葬師緩緩地走進空地,打開布包,白骨和肉血便散落一地。他手執石斧,把骨肉打得稀爛,以方便禿鷲啄食,同時把先人的靈魂帶往極樂。回想走上小山時,腳下那些白色碎片,就是從禿鷲口中跌出來的白骨碎片 — 一切關於天葬的景象,只剩這些零碎的片段,倒是那股惡臭,一種只會從屍身發出的味道,卻永遠烙印在我腦海。人的身軀,終究只是一堆血肉,甚麼也帶不走,「臭皮囊」最終化成糞土,或變作樹木的養份,或成為禿鷲的食物,甚或燒成灰燼。那是二零零四年,我的畢業旅行,也是我第一次背包遊 — 這是喜愛旅遊的源起,也是我人生的起點。 花光積蓄 歐遊一年 工作了八年,想給自己一個更大的挑戰。在二十九歲那年,我決定辭工,放下一切到外國去生活一年。早於一年前,我已開始讀德文。考到初階證書後,便申請德國的工作假期簽證(Working Holiday Visa)。五年前的二月,我拿着所有積蓄,飛往柏林。那年天氣特別差,整個月都下着雪,街上灰蒙蒙的。我雖然學過德文,但程度只夠作簡單溝通,根本沒有公司會聘請,最終只能到中菜餐館比較集中的地區,挨家挨戶拍門問是否請人。找了兩個多月,終於碰見一家有空缺的。因為德語不流利,我只能在水吧負責洗杯、預備飲品和清潔等工作。 雖然只做了六個星期,卻是個難得的體驗。我在當地作為二等公民,還要被中國人老闆剝削和壓榨,以低於標準工資一半,做雙倍的工作。成為勞動階層,是我前所未有的體驗。如果我一直留在香港這個安舒區,我根本不會重新檢視自己的身份認同。人的身份從來都是流動的,在不同的環境下,就會遇到不同對待。在香港或許你是大學畢業生,有穩定的工作;但到了外地,你只是另一個廉價勞工。當身份認同改變了,就要隨時改變自己的態度和想法。我學會了體恤和敬佩所有付出勞力而換取報酬的人,真切地了解工作無分貴賤的意義,最重要的額外收穫,是學會了把杯碟洗得閃閃發亮。 從我懷中流逝的溫熱 雖然好不容易申請到工作簽證,但由始至終我遠赴德國都不是為了洗碗。在柏林三個月後,我再次揹上背包,跑到另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。愛爾蘭的五月依然寒冷,我穿着厚厚的毛衣,從都柏林坐了個多小時車,到了郊外的一條小村。農夫John從農舍走出來,帶我走進屋裏、上了二樓,就是我往後兩個月的睡房。從現代化的都柏林來到農場,只為一嘗打工換宿的滋味。時值初夏,農場有很多雜務,例如把收割了的禾草捆起來,或是到農場周圍逐處檢查鐵網是否有破爛,還有最直接的剪雜草。那兩個月農場生活中,最令我難忘的,卻是一隻大頭小羊。牠只有幾天大,卻不太懂走路,我常常發現牠躺在路中。羊媽媽已好幾次把牠遺棄,我試過抱牠找媽媽,牠連叫的力氣也沒有。怎料一天早上,我竟在路上找到牠的屍骸,羊媽媽站在旁,看着我,叫了幾聲。可憐的小羊,眼珠被鳥兒吃掉了,昨天還躺在我懷內、依然溫暖的身軀,今天卻變成一副骨頭和血肉分離的軀殼。這當然是大自然定律,但當我曾經感受過的溫熱、那麼珍而重之的一條小生命,竟這樣不動聲色地離開。生命是如此脆弱,回想人生種種際遇,遷怒過的人、遭遇過的挫敗,其實根本不算甚麼。 性格獨特的巴爾幹半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