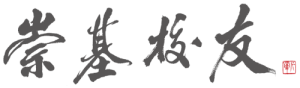三十多年的情誼與承傳 —— 甄玉媚(1988/社會工作) / 文質宿生會主席(1987)
我一直嚮往大學住宿的機會,感謝當年崇基「四年一宿」的政策,讓我可以達成願望,在大二時搬進最心儀的文質堂。當年我既可在星夜蟬鳴下坐在窗前沉思,又可以經常在樓層間串門子,更難忘是一邊煮宵夜、一邊與閨蜜們談心……那三年,實在是十分幸福的歲月。 每晚上演的愛情映畫戲 我在學時仍是手提電話還未普及的年代,那時每層樓只有一個在茶水間的固網電話供全層女生共用。只是我們文質堂標緻的可人兒實在太多,每晚排隊「煲電話粥」的場景一直上演至凌晨。不過大家都能互相體諒,天長地久的情話也要在十五分鐘內說完。當然,拿着話筒哭哭啼啼,歇斯底里的場面也時有出現,或許當年你也曾遇上此情景而送上溫暖的慰問呢! 文質第一湯 身為堂主,為文質姊妹謀福利是我的首要任務。每年的迎新送舊大會和聚餐自是最受歡迎,整個宿生會一起「落手落腳」炮製豐富大餐,換來眾人的讚美感謝聲,就是我們最佳的動力。一次「糖水會」前,莊員們有感煲糖水太普通,於是建議煲老火湯,最後 Miss Tsang (舍監江曾碧珠女士)特地開車載我到沙田街市買了四隻雞,加上雪耳,如此這般便開啟了文質湯水會的新時代。 友誼不分國界 曾經有位來自秘魯的交流生入住文質,她圓圓的眼睛配上膚色通透的鵝蛋臉,最吸引何宿的男生;加上她乖巧親切的性格,大家當然很熱衷跟她作文化交流。我們教她說廣東話,她就回敬我們西班牙語;我們教她搓湯丸,她就分享秘魯的炸吞拿魚球小食 — 那是一種用上吞拿魚、碎洋蔥再加上鮮奶及粟粉搓成球狀,然後拿去炸的小食,至今我對那甘香鬆脆的滋味仍然記憶猶新。 永遠熱血的傅盃 動靜皆宜的文質姊妹,配上粗獷豪邁的應林兄弟,擦出的是不一樣的火花。兩宿先一起舉行誓師大會,之後在傅盃場上攜手悉力以赴,互相支持。過程中最珍貴的是彼此建立的友誼和真誠的交往。當然,最後文質應林也以實力取得多項冠軍,成為第九屆傅盃的大贏家。 與應林兄弟的誓師大會 感恩承傳 三十年後我的女兒也幸運地入讀中大,加入崇基,亦在「四年一宿」政策下入住文質堂。我陪着她再次走進文質,地方整潔光亮,那種親切的感覺,連同當日種種歡樂的片段,再次呈現腦海中。今天,在飛機上執筆回味那些年的往事,同行的也正是在文質的室友Bonnie及宿友Connie和Dora。四個閨蜜,三十多年的情誼,是緣份,也是上天的恩賜。 文質一九八八年社工系畢業的閨蜜ABCD四人今年五月中結伴遊泰國(由右至左):Angi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