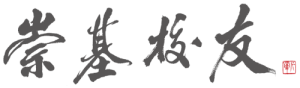打開心窗 尋找愉悅 —— 陳秀芬校友(1991/醫學)
訪問:鄭穎茵(2006/中文) 陳秀芬(1991/醫學)是精神科專科醫生,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名譽臨床副教授,有超過二十年治療情緒病及精神問題的經驗。陳校友亦是國際認可的榮格學派心理分析師,近年專注發展精神科醫生的心理治療培訓工作。公餘時間陳校友熱愛運動,常到不同地方參加馬拉松比賽,並屢獲佳績。 精神健康問題近年在香港愈來愈普遍*,為甚麼會有這個趨勢? 香港社會變化快,政治、經濟環境本身已瞬息萬變,加上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、隔代矛盾、資源競爭等問題,都大大加重了我們的精神壓力。當大家容易感到生活徬徨無助,便有機會引發各種情緒病,例如焦慮症或抑鬱症。 其實每個崗位都有各自的困難,不論年齡背景職業都不能倖免。以學業壓力為例,近年情緒病有年輕化跡象,小朋友的求助個案每年都不斷上升。雖然現在物質生活豐富,但小朋友面對的競爭、家人的期望和要求卻同時增加。父母的焦慮會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了小朋友。如果父母經常把「未來的世界很可怕」、「總要贏在起跑線」等觀念灌輸給小朋友,那麼他們又何以建立安全感呢﹖ 我遇過一位小朋友,每天都感到非常驚恐,而且不願上學。原來媽媽對他的家課要求甚高,如果被發現做錯就要全版擦去重做。媽媽的原意是要讓小朋友培養認真做事的習慣,但我們試試代入小朋友的處境:每份家課都要重做幾次,很自然他會改出眼淚來。如果他生活上其他方面都要應付類似的要求,那麼他每天就是不斷重做和改正。這不單是修正某一錯處,而是令他以為整個人生都是個錯誤,大大影響了自尊心和自我形象,成為他成長中的困局。 即使一般人不一定經歷過兒時的深層次創傷,但在人生階段的轉變關口,一時應付不來也可能引起情緒問題。有一位幼稚園教師,她常常擔心自己對小朋友太兇惡,又怕做錯事連累同事,工作壓力大得令她害怕上班。那時她剛結婚,面對人生角色轉變,同時又因照顧父母時間減少而感到內疚。這些重大轉變令她患上焦慮症、強逼症和抑鬱症。可幸經過一年的藥物和心理治療,她漸漸康復並適應新生活,慢慢兼顧自己不同的角色和工作。 陳校友熱心推廣精神健康教育,二零一八年五月她為崇基學院校友會晚餐講座擔任嘉賓講者,分享「從夢中得心靈成長之道」。 精神科治療的過程是怎樣的? 精神科治療主要分為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。心理治療的時間長短不一,有些個案只需數月,病人在醫生協助下便可以自我調節過來;如果問題牽涉一些深層次創傷或缺欠,治療時間可能需要一至兩年,甚或更長時間。 成人的個人形象和性格都是從小形成,主要與家庭教育和遭遇有關,這些背景就像建築房子的支撐骨架,長大就是把經驗逐漸建構上去。對自己缺乏信心的人,不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好;他們不相信自己的情緒訊息,凡事均從負面去想,同時又很介意別人的目光,難以信任別人。這些問題需要心理治療,透過整合意識和潛意識,再透過圖像訊息了解根源,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強項和可能性,從而改變對自己看法,進一步改善與家人的關係。心理治療就是讓病人慢慢建立對人的信任及將來的盼望,重新找到自己的立腳點,讓他們重拾重心,可以感受到自在、滿足、愉悅。治療過程中,醫生會讓病人了解各種可自我支援的方法,內外整合,好像把不同資源和工具放進病人的「百寶袋」裏。 有些病人會自行停藥或沒有再見醫生,可能會引致病情反覆。其實他們在痊癒後需要較長的穩固期。他們不斷掙扎,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去站穩陣腳,只是未有周詳計劃便自行決定停藥。我們應以同理心看待,欣賞他們的良好意願和動機,不應加以責怪。經過心理治療後,將來若他們再遇到困難,都可以在「百寶袋」中拿工具來應用,也會比較清楚甚麼時候要再尋求專業人士協助。 陳校友曾到瑞士學習榮格心理治療,過程中由老師對她進行心理治療,讓她自己也成為受助者。畢業的時候,老師把這個塑像送給她,希望她謹記作為受助者的經驗。塑像是老師的母親留下的珍藏,有承傳意義。大象的母性亦有照顧孩子、承載別人的意思。